译者手记|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没有20世纪的法国文学
- 信托知识
- 2025-04-07 14:22:05
- 7
加缪曾经断言,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没有20世纪的法国文学。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加缪尤对《群魔》推崇备至,将其与《奥德赛》《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以及莎士比亚戏剧并列为世界文学的思想巅峰。在20岁遇见《群魔》之后,加缪从中得到了持续毕生的“震撼”与“哺养”。46岁那年,在耗费数年心力,终将《群魔》搬上法国戏剧舞台之际,加缪写道:“之所以说《群魔》是一部预言书,不仅仅因为它宣告了我们的虚无主义,还因为它表达了万分痛苦或死亡的灵魂。这些灵魂不能够爱,又为不能够爱而痛苦,虽有愿望却又无法产生信仰,这也正是充斥于当今社会和思想界的灵魂。”
一、主题概述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政治倾向性的长篇小说,《群魔》曾长期被定性为“政治谤书”。不可否认,在构思之初,作家的确曾想以“涅恰耶夫谋杀案”为皮鞭,对俄国西欧派和虚无主义者给予“最后的鞭笞”,为此甚至不惜牺牲艺术性。但随着创作的进展,艺术逻辑开始发挥作用,思想性和艺术性非但没有被政治倾向性抹杀,反而冲淡、平衡了政治倾向性,促使作家在政治批判之外,又加入了爱的悲剧、道德救赎两大主线,从而铸就了一部犀利而深邃、现世性与普世性并重的不朽杰作。
小说政治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两代人: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西欧派和60年代的虚无主义者。前者以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卡尔马济诺夫、冯·连布克等人为代表,后者以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五人小组成员等为代表。二者在思想上父子相承:正是前者在全盘西化道路上对俄国民族土壤和传统东正教信仰的脱离与背弃,导致了否定一切进而毁灭一切的后者的诞生。但与此同时,前者拒不承认其对后者罪行负有道义责任,后者则矢口否认前者对自己的历史影响,双方都竭力与对方划清界限。这种畸形的父子纠葛与代际冲突,在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与亲生儿子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以及曾经的爱徒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矛盾关系中得到了清晰展示。站在二者对立面的沙托夫是新斯拉夫主义者和根基主义者的代表,其核心思想便是以俄罗斯为唯一的“载神民族”,以新神之名革新世界、拯救世界。沙托夫与韦尔霍文斯基父子的争论是土壤派与西欧派及虚无主义者思想论战的真实反映,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团伙对沙托夫的蓄意谋杀则是作家对虚无主义者戕害祖国与人民的严厉控诉。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所谓地狱,就是无法再爱的痛苦。”《群魔》正是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解: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长达20年的柏拉图式精神暧昧无疾而终;沙托夫与妻子在破镜重圆,即将奔向新生活之际双双殒命;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则更是以一己之力,为众多美好女性构建了种种地狱。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对他的爱是慈母对逆子的卑微之爱,爱与惧都渗进血液里。跛脚女人列比亚德金娜对他的爱是虚妄之爱,是一个被踩在污泥里的疯女人对钻石的幻想、对雄鹰的仰望。家仆之女达莎与他心灵投契,却无力逾越主仆尊卑的鸿沟,这是不堪一击的纯粹之爱。达莎很像《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只是她未曾经历足够多的苦难,因而也就没有足够多的坚忍,无法像索尼娅拯救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拯救斯塔夫罗金。千金小姐莉莎与他门当户对却精神隔膜,她就像只骄傲的飞蛾,不顾一切地扑向一团烈火,却在翅膀被燎焦之后转身飞走:这是不能自已却又无法忘我的痛苦之爱。四位女性的身份素养、气质性格、人生际遇千差万别,代表着在爱的地狱中苦苦挣扎的广大魂灵。而其地狱的制造者无疑正是斯塔夫罗金,尽管他本人同时也是地狱的承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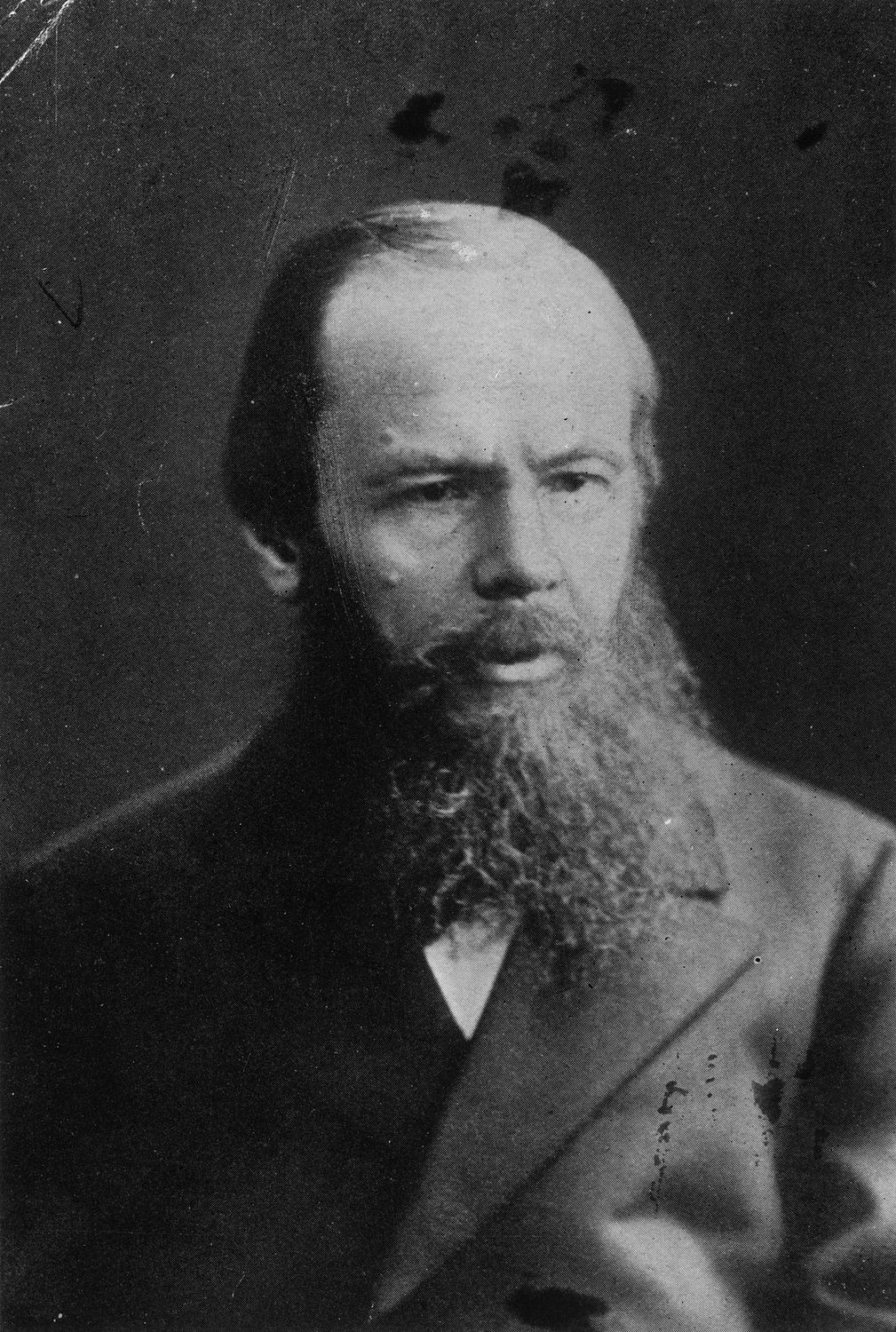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
岂止女性,书中的男性人物同样对斯塔夫罗金爱恨交加:始终在精神上跪伏于他的沙托夫当众打了他一记耳光,妄图自杀成神的狂人基里洛夫称其在自己生命中意义重大,就连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也甘愿奉他为精神偶像。基里洛夫和沙托夫,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思想极端皆是拜他所赐,二者恰似斯塔夫罗金精神的一体两面:如果说沙托夫是信神而寻神的斯塔夫罗金,那么基里洛夫则是寻神而不得,继而否定神的存在,并妄图取而代之的斯塔夫罗金;二者与其说是前后相承的思想历程,莫如说是此消彼长的精神冲突。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则被斯塔夫罗金毁灭一切的兽性本能所吸引。换言之,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三位一体”,分别象征着斯塔夫罗金的神性、魔性与兽性。斯塔夫罗金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最深刻、最复杂的人物形象之一,在他身上,神性、魔性、兽性、人性均扩张至极限,以最大的力度纠缠冲突,共同构成了深奥费解、神秘极端的斯塔夫罗金性格。而破解斯塔夫罗金之谜,揭示其精神冒险与死亡,就构成了小说的道德救赎主线。
政治阴谋、爱的悲剧、道德救赎这三条叙事线索彼此交织,其交点正是斯塔夫罗金。作为思想探索者、秩序反抗者和超人主义者,他因丧失了与俄国民族土壤的血脉联系而无从获得坚定彻底的信仰,于是索性抛弃了一切道德准绳,在善与恶、真与伪、崇高与卑鄙、信仰与虚无的极端反复跳跃。他了解自己的悲剧所在,却无力自我救赎。作家为这个他“从心底抠出的”“兼具俄国性与典型性”的“真正主人公”安排了两位拯救者。一个是土壤派的代表者沙托夫,和《罪与罚》中的索尼娅一样,他建议斯塔夫罗金去亲吻大地。作家借跛脚疯女人之口说:“圣母就是伟大的大地母亲,人的大欢喜就在于此。大地上的任何痛苦和眼泪都是我们的欢喜,只要你能用自己的眼泪把脚下的大地浇灌到一尺深,你就能立刻获得大欢喜。那时你将不再有任何、任何的苦处,这就是神启。”另一个是东正教信仰的化身吉洪神父,他竭力劝解斯塔夫罗金放弃自毁,借由皈依东正教信仰获得救赎。扎根民族土壤,皈依正教信仰,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国虚无主义者开出的药方,奈何附魔之猪注定闯下悬崖,溺死深海,从而换取“伟大的、亲爱的病人”——俄国——“坐在耶稣脚前”。作家通过揭示群魔毁灭的必然,寄托了对于复兴俄国、救赎世界的希望。
毋庸讳言,在作家讽刺性描写的主人公身上,的确有着同时代众多知名人物,如格拉诺夫斯基、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涅恰耶夫等人的身影,但并不能因此将人物与其原型划等号,进而将小说视为一部应时短命的政治谤书;恰恰相反,这些人物均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有可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诚如加缪所言,《群魔》中的人物既不怪诞,也不荒唐,而是有着与我们每个人相似的心灵。他们可憎可爱,可恨可怜,可鄙可敬,可笑可骂,可歌可唾,但无不沿着“痛苦和温情的线路”,“行进在这个巨大而可笑的、躁动的、充满喧嚣和暴力的世界上”。
二、世界影响
作为一部为世界小说史开创新篇章的垂范之作,《群魔》对20世纪的世界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29年诺奖得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应恰如其分》一文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他者心灵的冷静如临床诊断般的深入剖析仅仅只是表象,其创作其实更像是一部心理抒情诗……是忏悔,是令人血液冻结的自白,是对自我良知的罪恶深处的无情揭露。”在他看来,冷酷而高傲的“超人”斯塔夫罗金无疑是世界文学画廊中最具致命吸引力的人物形象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
1947年诺奖得主、法国作家纪德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尊为比列夫·托尔斯泰更伟岸的高峰,将《群魔》奉为“伟大小说家最有力、最杰出的作品”。在其长篇小说《伪币制造者》(1926)中不难发现《群魔》的烙印。
1957年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哲学家加缪更是从《群魔》中汲取了无比丰富的思想与艺术给养。在《西西弗的神话》(1942)一文中,加缪以荒诞者斯塔夫罗金和基里洛夫的自杀哲学为基点,论证了存在主义式的斯多葛主义,以对抗生命的荒诞。剧作《卡利古拉》(1939)阐释了“崇高自杀”主题,剧作《正义者》(1949)和哲学随笔《反抗者》(1951)则探讨了俄国虚无主义和希加列夫习气。长篇小说《鼠疫》(1947)中的“纪事体”和《堕落》(1956)中的“自白体”叙事模式,亦皆从《群魔》借鉴而来。
1994年诺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同样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特别是《群魔》的影响。其长篇小说代表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中主人公鹰四在向哥哥坦白罪孽后自杀的情节,《别了,我的书》(2005)中的五人小组谋杀事件,《水死》(2009)中的“人神”思想等无不源自《群魔》。
作为一部思想与艺术交相辉映的鸿篇巨制,《群魔》因其复杂深刻的戏剧冲突、饱满充沛的戏剧张力而备受戏剧界青睐,一百多年来被各国戏剧家不断演绎,成为世界舞台上久演不衰、常演常新的经典之作。
1907年,圣彼得堡上演了首部话剧版《群魔》。该剧带有鲜明的反虚无主义性质,竭力凸显对地下革命者及自由思想者的漫画式讽刺。自1912年8月起,俄国戏剧界泰斗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开始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紧锣密鼓筹排新版《群魔》。翌年9月,高尔基接连发表《论卡拉马佐夫习气》和《再论卡拉马佐夫习气》两文,以社会教益及民众精神健康为名,强烈抵制《群魔》上演。高尔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定义为“恶毒之天才对俄国民族性格负面特征之天才概括”,称其作为书籍阅读尚可,但用于舞台呈现则是于社会有害且不合时宜的。高尔基的言论引发了轩然大波,库普林、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古勃、列米佐夫、安德烈耶夫等一众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予以谴责。尽管丹钦科版《群魔》于1913年10月23日在圣彼得堡如期上演,但在国外巡演时却遭遇了不小阻力:该剧在维也纳自由剧院仅公演一场,便因“抨击俄国自由运动”而被迫停演,在柏林更是未能登台。1947年,苏联著名陀学研究家多利宁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忆及这场论战时曾说:“我相信,安德烈耶夫当年对高尔基的指责——“你自己不也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才学会了暴动吗?”——总有一天会凸显其正确性。……高尔基的这些言论无疑是踩在了他自己的喉咙上。……他造成的危害是旷日持久且无可挽回的。”
1930年,捷克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新版《群魔》再度引发激烈论战。以捷克作家尤·伏契克为首的反对阵营照搬了高尔基当年的社会政治学观点,捷克女作家玛·马耶罗娃则撰文驳斥:“我从不认为《群魔》是悲观主义者的诽谤或者撒旦式的捏造,而只是作家对他所看到、所感受到的包围在自己身边的邪恶力量的严厉回应。”
1939年,由戏剧导演米哈伊尔·契诃夫(安东·契诃夫之侄)执导的话剧在美国百老汇上演。该剧在《群魔》之外,融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长篇和通信,上演后引起巨大反响,赞誉声与批评声同等激烈。
1959年1月30日,由加缪改编的戏剧《附魔者》在法国巴黎首演。该剧遵循了原著“由讽刺喜剧走向正剧,再走向悲剧”的内部运动逻辑,以《斯塔夫罗金的自白》为结构中心,旨在凸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共产主义,即所有人的道德责任”。加缪此语明显呼应了吉洪神父的话:“每个人的罪过都是针对所有人的,每个人都对他者的罪过负有一定责任。”《附魔者》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多国上演。
由波兰著名导演、编剧,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安杰伊·瓦伊达执导的话剧版《群魔》主要展现了贵族自由派如何演变为危险分子。该剧于1971年6月在克拉科夫市老剧院首演,1973年在伦敦荣获国际大奖。其充满隐喻意味的舞台设计令人印象深刻:黑云和黑马疾驰在咕嘟冒泡的沼泽之上,一群搬动道具的黑衣人在偷听众演员的自白之后,踏着邪恶的舞步将其踩翻在地。据瓦伊达解释,这群黑衣人并非“群魔”,而只是事件的见证者,但他们却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威压,迫使演员将悲剧进行到底。“演员眼中的恐惧——这便是我的作品。”后来瓦伊达还曾将《群魔》翻拍为电影。
在苏联,《群魔》直至1988年才得以重返戏剧舞台。在诸多新版本中,剧作家马·罗佐夫斯基创造性地将《罪与罚》与《群魔》串连起来,让作家笔下的三位“双重人格”——拉斯科尔尼科夫、斯维德里盖洛夫和斯塔夫罗金同台演绎,并且后两者由同一位演员扮演,甚至连妆容都未改变。罗佐夫斯基意在表明,正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超人”思想催生了“群魔”,进而产生了撒旦式的“革命诈骗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
百余年的文学阐释与戏剧演绎雄辩地证明,《群魔》是一部永不过时的预言之书。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群魔》是为未来而写,其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从前,莫如说是当下。”
三、译本介绍
受苏联对《群魔》批判态度的影响,国内对《群魔》的译介远远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长篇。直至1979年,台湾远景出版社才推出首个繁体中文版,由孟祥森转译自英文,书名《附魔者》。四年之后,首个简体中文版才在大陆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南江译)。此后又相继问世三个简体中译本,分别为娄自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初版),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初版),冯昭玙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初版)。其中,除娄自良先生将书名译为《鬼》之外,其余三位先生均译为《群魔》。
娄先生将书名“Бесы”译为《鬼》,原因有二。首先,福音书中的“Бес”通译为“鬼”,而非“魔”;其次,“‘群魔’脱胎于四字词组‘群魔乱舞’,泛指一群坏人猖狂活动。如此,比喻的深远含义便荡然无存”。以上考量自有其道理,但依笔者之见,译成《鬼》未必就妥。首先,“鬼”在汉语言文化语境中联想意义丰富,但最根深蒂固者莫过于“鬼魂”,而圣经文本中的“鬼”则更多指“魔鬼”;其次,原书名“Бесы”为复数,而“鬼”通常会被视为单数。
“Бесы”的典故分别见诸于《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两福音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作家所引用的经文出自《路加福音》,但《马可福音》对该典故的记述更为完整(以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5:8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阿,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5:9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
5:15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
由此可见,小说书名或可译为《群鬼》,以便在强调复数意义的同时,尽量将其限定于圣经语境,避免与汉语言文化语境中的“鬼魂”或者“群魔乱舞”发生联想。但《群魔》一名毕竟流传多年,贸然更名难度不小。笔者为此曾求教于著名翻译家刘文飞教授和陀学研究家王志耕教授,并与本书责编张晨女士详加商榷,最终决定仍然沿用《群魔》。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补遗:在吉洪处》一章的坎坷命运,四个汉译本在内容上有所出入。该章是小说中心人物(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与灵魂人物(吉洪神父)的直接对话,深入探讨了信与不信、罪与救赎等核心主题,其之于《群魔》恰如《宗教大法官》之于《卡拉马佐夫兄弟》。按照作家最初的构想,该章本应作为小说的思想中心和结构中心,放在第二部第九章,即《伊万王子》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遭搜查》中间,不料却在付印之际被《俄国导报》主编米·尼·卡特科夫以“包含诱奸少女等淫秽情节”为由删去。尽管作家百般协调,反复删改,但在其生前始终未能发表。直至1922年,该章才首次以补遗形式与俄国读者见面。这当然是臭名昭著的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的累累罪行之一。但依笔者之见,将该章置于书末而非中间,并未减损,反而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因为该章堪称揭秘之章,其中的《斯塔夫罗金的自白》更是以人物内视角直击了上帝与魔鬼在其内心深处的激烈搏斗,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其病态灵魂。倘若将其置于小说中间,则围绕在斯塔夫罗金身上的诸多悬念被提前打破,艺术张力势必大打折扣。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至少在这件事上,书刊审查鬼使神差地干了件好事。
四译本中,南江译本问世最早,后经多次再版,但始终未能补译《在吉洪处》一章,实为遗珠之憾。其余三译本虽均有此章,但因所用底本差异,在位置和内容上有所不同。臧译和冯译均参照俄文版,将该章置于书末;娄译则将该章回归原位,以期复现作家的最初构思。就内容而言,娄译版在《斯塔夫罗金的自白》一节略有缺失,比如少了关于偷钱包的情节,以及对于偷窃、决斗、挨耳光等行为的心理剖析——这些“无耻而疯狂”的举动带给他同等强烈的罪感、耻感与快感。最大的出入乃在于诱奸事件。在臧译和冯译中,斯塔夫罗金对于诱奸罪行供认不讳,并以直白的文字复现了这一场景;而在娄译中,自白书恰巧在猥亵开始时出现缺页,斯塔夫罗金对吉洪神父辩称,该页正在接受书刊审查,并矢口否认诱奸罪行。另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差异:在娄译中,斯塔夫罗金找到误以为被偷的折叠刀,是在无辜蒙冤的小女孩惨遭母亲毒打之后;而在臧译和冯译中,斯塔夫罗金还在女房东扑向扫帚之时,便已寻见了折叠刀,但他却在突如其来的邪恶图谋之下,默许甚至怂恿了体罚的发生。两相对照,无疑臧冯二译本中的斯塔夫罗金更为深刻复杂,更符合作家对于人物的设定。
四、翻译体会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思想论战往往以报刊为阵地展开。因此,作家常以报刊为道具反映人物的政治立场,或借助刊名的双关意展开讽刺。比如在本书第三部第二章第三节,在省长夫人张罗的筹款盛会上,著名作家卡尔马济诺夫编排了一场“文学卡德利尔舞”,由化妆舞者扮演不同政治立场的报刊:一位蓄着令人生敬的花白胡子的老者,嘴里不时发出某些温和而嘶哑的“呼声”,以此讽喻原属温和自由主义派,却时常附和反动报刊的《呼声报》(《Голос》);“正直的俄国思想”则被塑造为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先生,身着燕尾服,戴着手套及镣铐,腋下夹着公文包,从中露出一本“卷宗”。“卷宗”对应的原文为“дело”,该词另有“事业”之意,暗指因具有革命民主倾向而备受迫害的进步月刊《事业》(《Дело》)。无独有偶,在第一部第二章第三节,当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在贵族俱乐部公然拽了年高德勋的加加诺夫先生的鼻子之后,老好人省长迫于俱乐部集体施压,不得不召见肇事者“哈尔王子”,对其予以劝诫。但出于对后者的畏怯,省长提前埋伏了两名帮手,其中有位体格壮硕的上校,佯装在隔壁房间读报,读的正是《呼声报》(《Голос》)。作家之所以选择这份报纸,除了表明上校乃至省长本人的政治立场之外,另有巧妙用意。在后文中,面对省长的逼问,斯塔夫罗金说了句“那就让我来告诉您是怎么回事吧”,然后凑到省长耳畔。写到上校此刻的反应时,作家说他“кашлянул за «Голосом»”。此处同样运用了“голос”一词的多义性,既可以理解为“他在《呼声报》后面咳了一声”,也可以理解为“他听到这话之后咳了一声”。
受限于语言差异,在处理此类语言游戏时,译者通常不得不取消双关意,只在必要时添加注释。但在后文中,我找到了一个翻译补偿的绝佳机会:当斯塔夫罗金一口咬住省长的耳朵尖时,省长大惊失色却不敢声张,两名帮手因视线被遮挡而不明就里,“只当两人是在说悄悄话”(“казалось, что те шепчутся”)。我灵机一动,将这句话翻成了“只当两人是在‘咬耳朵’”,借助“咬耳朵”一词的多义性,在翻译补偿的同时,复刻了该场景的戏谑效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善于在大的篇章布局中设置悬念,也常在小的语段中暗藏机锋。比如,在本书第二部第五章第二节,在介绍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一行人的出游目的时,有这样一个长句(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редприятие было эксцентрическое: все отправлялись за реку, в дом купца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у которого во флигеле, вот уж лет с десять, проживал на покое, в довольстве и в холе, известный не только у нас, но и по окрестным губерниям и даже в столицах Семен Яковлевич, наш блаженныйи пророчествующий.
对于这种层层嵌套的倒装式复合长句,译者通常会采取“长句拆短句,倒装改正装”的处理思路。比如臧译如下(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他们要干的事的确有点离谱:他们大家是到河对岸商人谢沃斯季亚诺夫家去,因为在他家的厢房里住着我们的一位神痴和先知谢苗·雅科夫列维奇。已经差不多十年了,他隐退在家,生活优裕,备受照顾,他不仅在我们这儿很出名,而且在附近各省,甚至在两大京城也极有名气。
其余三译本的处理与此基本一致。这种处理的确能让译文流畅好读,但在语气、意蕴上却与原文相去甚远。由于倒装句的缘故,原文读者在读到此句时,对于厢房住客的身份是留有悬念的,而作家又故意使用一长串的定语,将悬念时间一再拖长,吊足了读者胃口,最后才蓦地丢出一个意料之外、饱含讽刺的谜底。因为在东正教文化语境中,所谓“блаженный”(与“юродивый”基本同义,通译“圣愚”)一定是居无定所、衣不蔽体、禁欲苦行、形销骨立的苦修士形象,而读者在前文中看到的却是——定居十年、生活安逸、盛名在外,这样的人居然被奉为圣愚,岂非莫大的讽刺吗?针对俄国民间圣愚崇拜泛滥的乱象,18世纪的圣徒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曾说:“一千个‘圣愚’里面,只有一个能称之为圣。”小说中的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正是这样一个伪圣愚形象。据作家夫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介绍,书中造访圣愚的情形源自作家本人对伊万·雅科夫列维奇(1783-1861)的拜访。后者虽被众多同时代人奉为圣愚和预言者,但始终未被俄国东正教会认可,一生中有47年时间在精神病院度过。小说中的“圣愚”谢苗·雅科夫列维奇身躯胖大、性情乖戾、言行疯癫,与谦仁博爱、充满神性智慧的吉洪神父形成鲜明对比,高下褒贬不言而喻。有基于此,我亦步亦趋地复制了原文句序,以传递其讽刺意味:
此次出行的确非比寻常:大家要到河对岸去,去商人谢沃斯季亚诺夫家,而在他家厢房,已有十年之久,一直安安生生地、舒舒服服地住着一位名震本省及邻近数省乃至两大帝都的大人物——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我们的圣愚和预言者。
文学是细节的艺术,文学翻译要求细节忠实,一词一句皆需推敲琢磨。比如,在第一部第四章第七节有一段关于教堂布道的场景描写,在写到布道结束,请出十字架时,四译本的表述分别如下:“把十字架拿了出来”“人们抬出了十字架”“神父拿出十字架”“扛出了十字架”。不难发现,四译本对于十字架的搬运人及具体搬运方式均给出了不同理解,相应地,十字架的大小轻重也必然大不相同。何以如此呢?原来,该句对应的原文是“и вынесли крест”。这个短句看似稀松平常,其实很值得玩味。首先,从语法角度来讲,该句属于“不定人称句”,即单纯强调行为本身,而忽略行为主体,其谓语动词虽为复数形式(вынесли),但行为发出者既可以是多个人,也可以是单个人。其次,“вынести”一词只强调移“出”,却并未限定具体搬运方式,拿出、抬出、扛出、搬出皆有可能。想要精确复现原文场景,必须了解东正教教堂布道的真实情形。经查阅视频及图片资料可知,用于此种场合的十字架多为半人高,木质,通常由一位神父双手捧住底部,并以额头抵住上部;有时另有两名神父护卫左右,双手托住中间神父的臂肘。因此,我将该句处理为“十字架被捧了出来”:“捧”字贴合动作,且饱含恭敬意味;以汉语被动句式翻译俄语不定人称句,则可回避行为主体的不确定性。概言之,适度翻译补偿,尽量遵从原文,追求细节忠实,这便是我在重译《群魔》过程中的三点粗浅体会。译事难,重译经典尤难。本书翻译历时两年,三审五校,不可谓不用心,但疏漏不足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纪德说:“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件终生大事。”博尔赫斯说:“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同发现爱情、发现大海,是我们生命中值得纪念的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则说:“读严肃的书;其余的交给生活。”在这部足够严肃的《群魔》付梓之际,惟愿读者诸君能够从中发现博尔赫斯曾经发现的爱情与大海,收获加缪曾经收获的震撼与哺养!
甲辰中秋于不足道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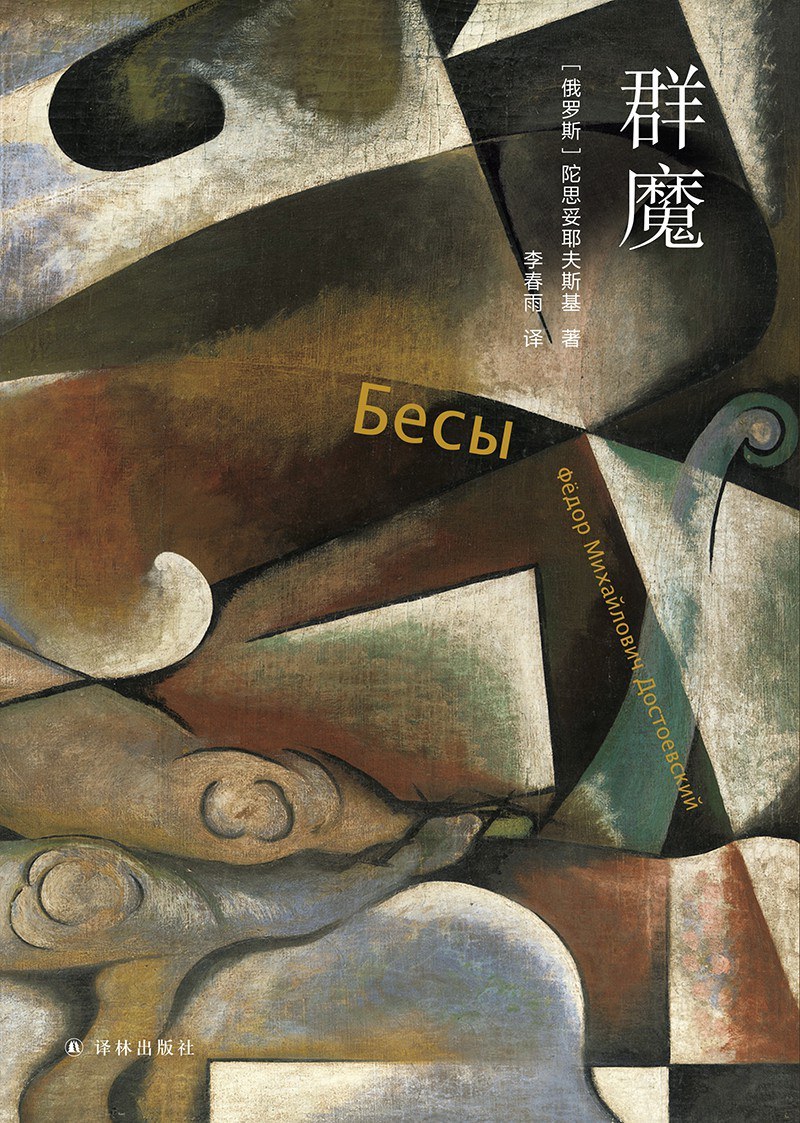
本文为《群魔》([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李春雨 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2月版)“译后记”,文中注释从略。
上一篇:4月26日股票操作策略
下一篇:低佣股票开户快速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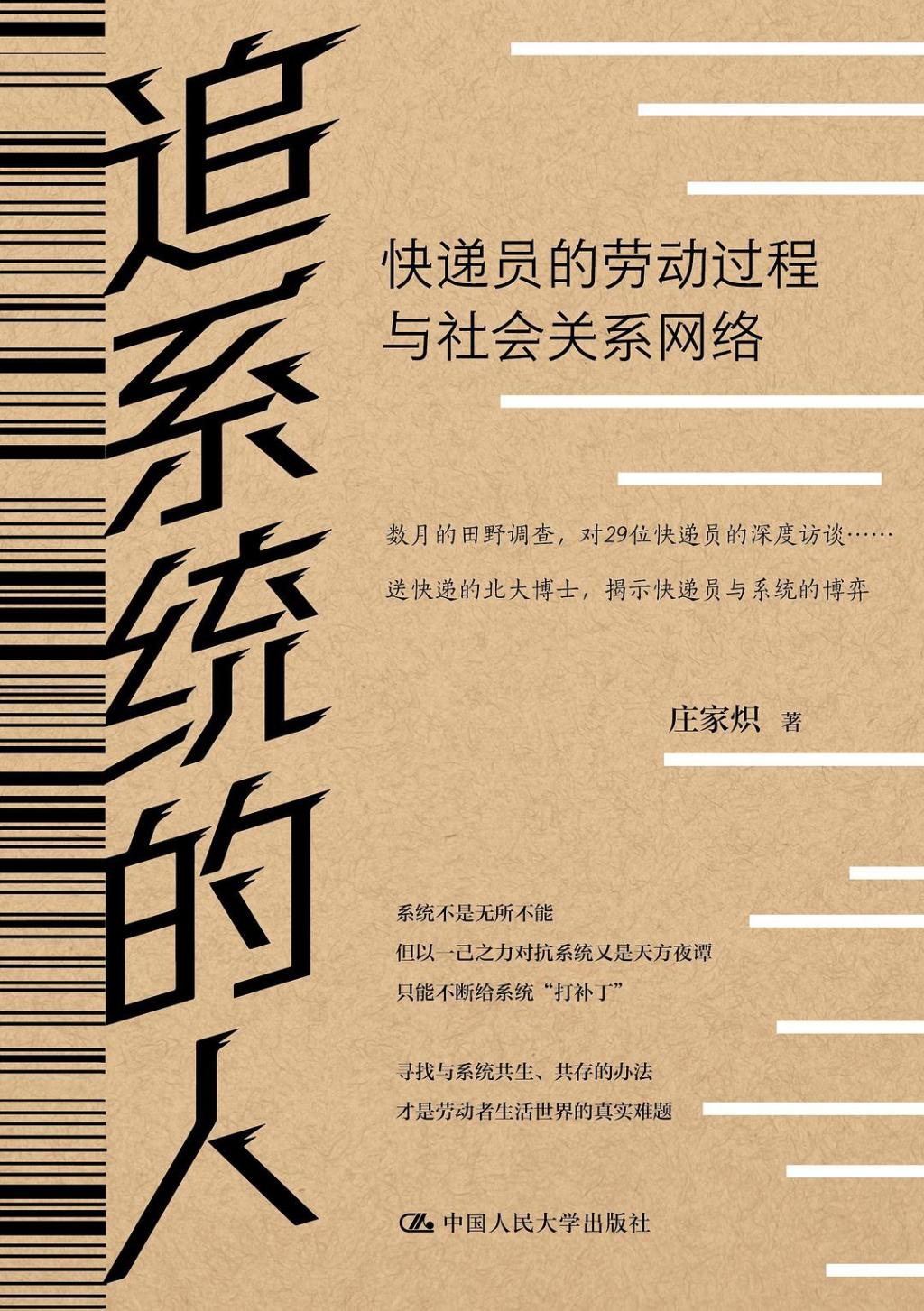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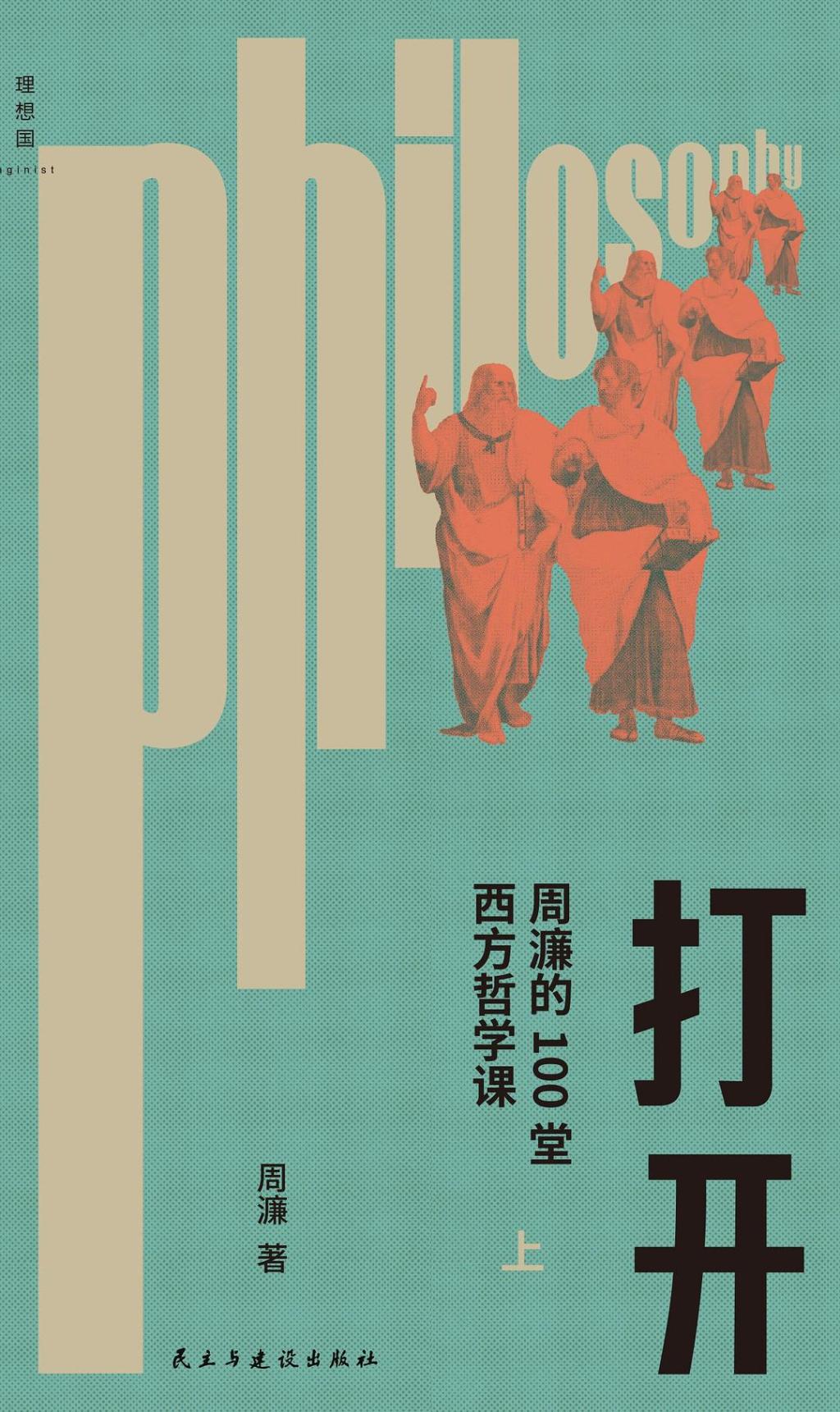




有话要说...